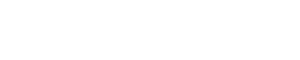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36节(1/2)
作品:《沉火不眠(生日当天我被我哥上了)》
发骂我是野种的画面,有时是她给我下跪求我放过她儿子的场景,但更多的是除夕那晚我哥背着我在雪地里一步一字的问话。
“哥看着你。好好看着你。背着你看每一年的冬樱,守着你一岁一岁地长大。好不好?”
我总是来不及说出那一个“好”字,我哥像是知道我不会回答一样,不给我留一点时间间隙,只自己一个人不停地重复着“好不好”,重复很多遍,听不到我的回答所以一遍比一遍急促,漫天烟花在他的催促中突然炸开,这时他在一颗冬樱树下止步,转头看着背上的我,满眼泪水:“你为什么不答应哥?”
我总在看到他眼睛那一刻醒来。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豫城找到了和家里那个一模一样的花瓶,枯枝插在里面,我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样把它擦得一尘不染,心里辟邪似的希望自己这样的“供奉”能驱散那些令我窒息的噩梦。
第二天我在教室上课,原历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准备大扫除,问要不要顺便把我房间收拾一下,对这句问候早已习以为常的我迅速给他发送了谢谢,而后继续投身进入题海战斗。
这份感激从与他合租开始一直持续到那天回家看到花瓶空空如也的那一秒。
我知道我完全没有理由去怪罪他的善意,任谁看了那个奇怪的花瓶都会顺手把里面的东西放进塑料口袋和垃圾一起扔掉,可那堆以惊慌和害怕为燃料的怒火还是不受控制地蔓延到了原历身上。
他面对我咆哮般的责问时满脸歉意的无措使我稍微找回了一丝理智,放低声音抱着一点“或许他只是把它放进某个抽屉而不是丢进垃圾桶”的侥幸问他把花瓶里的东西收到了哪里。
最后我还是逃不过站在楼下那七个齐腰的绿色垃圾桶面前。
那天下午的居民楼下有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把半截身子埋进垃圾桶里,像个捡破烂的流浪汉一样挨个挨个拆开里面的垃圾袋翻翻找找。数量过多的垃圾使他不得不把其中已经被他检查过的大半部分拿出来放到地上,因为下雨,当时以他为中心的方圆几米,只要靠近就能闻到一大股被空气恶意传播的酸馊臭味,所有要通过那里回家的人都翻着白眼绕道而行,而他终于在祸害了第三个垃圾桶以后终止了自己的恶行。
如果你愿意走近一点,会发现他佝偻在那堆垃圾里面,怀里抱着一根短短的枯枝,虽然分不清他脸上成股流下的是泪水还是雨水,但总能听见他失心疯一样喋喋不休的道歉,抱着一根茶褐色花枝麻木地喃喃自语。
他对着一根树枝叫哥,有时也会叫两声齐晗。
他在不停地说对不起。
那个年轻人叫齐野。
28
2013年10月26号
哥,我昨天差点把花枝弄丢了。
还为此向原历发了一大通脾气,其实明明不是人家的错。
后来我请他去酒吧喝酒道歉,结果他说我喝醉了发酒疯,大半夜在乾江大桥唱我住长江头。
2013年11月8号
哥,20岁了。
生日快乐,记得吃蛋糕,别给我留了。
2014年1月30号
哥,新年快乐。
别再在梦里问我了。
我答应你。
2014年5月8号
没有齐晗的第一个生日。
生日快……
算了,不快乐。
/
我没有想到高考过后胡遥会联系上我。
那是六月九号的凌晨。
原来过去的这一年上天没有眷顾我们四个中的任何一个人。
她们的事终究还是被捕风捉影的老师发现并且告知了家长———当然,只有成鞠的家长了。
于是在距离高考来临的前两个月,成鞠被迫休学出国,从此归来之时遥遥无期。
她让她等她。
到后半夜我实在分辨不清她在说些什么,从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来听她那时应该已经烂醉如泥。
我一直没有挂电话,放在耳边的听筒里不断传出一贯冷静理智的胡遥疯狂嘶哑的哭嚎:“她说她可以什么也不要…只要我一句话,她就跟我走……只要我一句话……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为什么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她第二天醒来还会是往常那个淡漠自如的胡遥,这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问她怎么找到我联系方式的,她说她干了当年我干的事———翻办公室
第36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