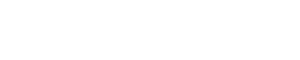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25节(1/2)
作品:《玫瑰少年》
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在时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没有笔、本子,只有些白纸片,裁得方方正正,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逼着我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他的命运也是不堪。我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宋霆是美好的,我却依然陷在温室里。
那一瞬间天旋地转,我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只不过这一次灵魂互换,好像我是他,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叛逆少年,他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他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数学课。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在他离开前的那一个下午,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 X_io_ng 膛,他含着我的 Ru /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像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肠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很重要,却绝非不可替代,如果我曾经疯狂地钟情于他,爱他胜过了自己,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我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江城的风俗认为,长江是天河水,通往四面八方,上穷碧落下黄泉。我知道这条河流不能通往北京,但我依然固执地想要告诉他,我要开始学会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有棱有角,再去与他相见。
2
我依然住在宋霆的家里,他给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足以保证我剩下的高中生活衣食无忧。在一个周末,我抽空回了一趟南区。
南区还是老样子。歪斜的铁栅门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变得更多,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 Yi-n 郁的天空,站在院子里才能望见。搭在院子里的大厨房塌了,棚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乎乎的坎。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
隔壁房间换了新的租客,是一个光头,姓程。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里浇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卧室里还是那张行军床。只是顶上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不像有人睡的样子。他咳嗽厉害了,连烟卷也不抽了。
母亲还是那样,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常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自来水还是金贵的。
时隔两个月,她看见了我,只是冷冷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回来了。
她忙着去做饭,没时间搭理我。
“妈,”我突然喊住她,“我有话想问你。”
她不耐烦地回头看着我,我张张嘴,问她:“……您,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我也不是讨厌你,
第25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