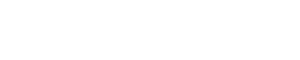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25节(1/2)
作品:《好巧,原来你们也不是土著(事业批病美人又在装娇吗)》
话地问道:“身份密契这么要命的东西,司阁主不毁了去,还留着做什么?”
司慎言看向纪满月,眼角露出点滴笑意:“这是司某与他的账,总该先留着账本儿,”杜泽成刚才去做什么了,他心知肚明,见他回来没炸刺儿,便道,“满月叨扰杜大人多日,司某先带他回去了。”
“且慢。”杜泽成道。
司慎言看他。
“点沧阁虏掠孩童的事情,又当如何论?”
司慎言叹了口气,道:“报案人何在?”
半盏茶的功夫,那叫钟正的孩子爹被带到花厅。
司慎言上下打量他,尚未开口,纪满月便打着晃儿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他还是有些趔趄,司慎言想扶他,被他看似不经意的扭身躲了开去。纪公子就这样弱风扶柳地晃到钟正身前,看着人,也不说话。
他脸色就没好过,熬刑七日,更惨白得跟鬼似的,额头伤口淌下的血迹还挂在脸上,嘴唇干裂开,口子深可见肉。
钟正本来已经心虚,见几日前还公子如玉的人,因为他一句话,被折腾成这副样子,更是不愿意与他对视。
“钟先生,心虚什么?”满月轻飘飘的说,露出一抹笑意。
他这副惨样子,不笑还好,一笑说不出的渗人。
钟正嘴硬,颤声道:“我没心虚,你不是好人,我心里怕你。”
纪满月上下打量他,幽幽道:“记得南泽湖畔,在下救令郎性命时,先生……身穿淡黄的棉布长衫,脚下广口布鞋,腰间悬得……”说着,他合上眼睛,似乎在回忆,突然就咳嗽起来,片刻平缓了气息,才继续道,“是个紫竹的‘节节高升’。”
他说完,手势在钟正身上比划了两个来回,那意思是,看先生如今——锦缎长袍,千层底的文生靴,腰间一块玉牌……
“青枫剑派出手也算阔绰。”满月微微颔首,笑着贴近这人身前,低声道。
接着,他撤后一步:“江湖恩怨,不该牵扯百姓,先生给句真话,这事儿从此罢了,若非不然……你不叫我痛快,我便先叫你不痛快。”
钟正是个普通百姓,被许小楼看准了脾性,才得以收买拿捏。
当日,他诬陷纪满月时,便觉得对方身形很像南泽湖畔救儿子性命的人,只不过箭在弦上,儿子在青枫剑派手上,自己又被半逼半游说的收了钱。
这会儿,终于反应片刻,转身向杜泽成跪下:“大人饶命,草民儿子在他人手上,受人逼迫,请大人为草民做主,只要能将幼子救回来,草民认罚认打!”说罢,磕头不断。
杜泽成皱眉不语。
司慎言看了看纪满月,他此刻只想赶快把人带回去休息,便道:“杜大人,此事本就是江湖纷争,不该惹大人伤神,让这位钟先生且随司某回去,事情了结之后,再来府衙销案。”
事至此时,杜泽成明白,他再揪住不放也是徒劳,摆摆手:“既然如此,本官还有军务,司阁主自便吧。”
就这样,满月终于站着出了府衙大门。
吴不好早就等在门口,见他出来时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开口便骂,也不知骂得是谁。
纪满月拍拍他肩膀,笑道:“三堂主,咱们还在衙门门口呢……”
吴不好不骂了,改了小声嘟囔:“老子想把害你的人砍成八八六十四块!”
钟正差点自台阶上拌下来。
纪满月见状想笑,可气息急促,又咳嗽起来,他头疼的紧,一咳嗽,脑袋就像是要炸开了似的。
吴不好扶他上马时,他几乎要坐不住——要是马儿跑起来,一个脱力,掉下来怎么办?三堂主正为此心焦,司慎言已经翻身上马,与纪满月同乘一骑,扯住缰绳就正好把人环在怀里。
纪满月惊了,刚要起身,腰间又一紧。
司慎言右手直接扣在他腰上,用力把人往怀里拢紧,不等对方再做反应,一夹马肚子,马儿便小跑着,远离开这晦气的地方。
纪满月强撑精神绷着身子,马儿颠簸得他坐不住,好几次,他都险些仰倒在司慎言肩上。要说满月现在这模样与风流潇洒半点不沾边。
顶多是沾满了泥泞被风雨摧打的玫瑰,还强撑着气力不愿凋落。
司慎言环着这人,不动声色地心跳快了——他对他的喜欢在这微妙的、亲近的距离中,悄无声息地发酵,莫名其妙地越发浓烈。
他偷偷喜欢的人,聪明,倔强,又戾烈。他知道,若是再相处下去,他还
第25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