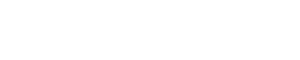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70节(1/2)
作品:《[英美]穿成夜枭的我选择跳槽[DC]》
年轻人脸上不可避免地浮现出痛苦和仇恨相交杂的表情,而且能看得出来,他不想让其他人、尤其是反转宇宙之外的人注意到这一点。布鲁斯移开视线,假装没看见利爪咬紧牙关时,从他每一块颤动着的面部肌肉中泄露出来的戾气。
半晌,理查德对他的问题避而不谈,硬邦邦地堪称缺乏礼貌地问道:“反监视者死了吗?”
**
反监视者死了吗?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实在是没别的可干。要说明下目前的情况——我按下按钮,量子本态炸弹确实是爆炸了。
人们对毁灭和死亡应该是有所预感的,就像我能确定之前发生的一切并非我的错觉,尽管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爆炸发生的瞬间,一种特殊的、来源不明的力量使我周围时间停滞、万物静止,唯独我站在凝固的时空中,像量子力学理论中那只著名的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
鉴于人类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尚且有限,该领域多数理论都处于玄学范畴,我毁灭世界也是两辈子头一次,不确定造成变动的到底是爆炸还是外力。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整个宇宙的生物连带着辛迪加都去到另一个维度了,我觉得也不差一时半会,就站在原地耐心地等着随便什么人过来把装着猫的容器盖掀开,不管它打算观测什么,至少我的结局已经写完了。
结果我先等来一把椅子。
来通知我们反监视者即将到来的自称是密特隆的人,一直坐在一把能飞的发着光的高背椅上。后来超霸去宇宙里搜集反监视者的讯息,顺带也了解了下密特隆,他坐着的那把椅子有个学名叫莫比乌斯椅,传说中可以回答其拥有者的一切问题。
也就是说,谁坐上去,谁就变成了近乎全知的神。
我花了很长时间和飘到我面前、其上空无一物的莫比乌斯椅大眼瞪小眼。
要说死亡是个过程,我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是这过程未免过于漫长。而且我有什么问题非要这把椅子给我答案呢?
我生前身后都是终结,所有人力所能及或不能及的难题,要么早已被我解决,要么随着这次爆炸成为了多元宇宙间的尘埃。事到临头只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宏大命题还有钻研的意义,譬如世界本质,又如我为什么而存在。难道还非得坐上去,听有罪者向虚空陈述他背后的累累血债,这忏悔之路才能通往安息之所吗?
太刻毒,以至于让人想想就心生畏怖,因此我没动。
椅子就也不动。
时间失去它的量度,我不知道我在这生与死的边缘等了多久,等得我耐心告罄,逐渐从对莫比乌斯椅的回避当中生出难以遏制的愤怒。这心情和我下定决心按下爆炸按钮时是不同的,但它们又都在向我反复强调,无论你愿意与否,能走的路皆只有一条。
所以我最终决定迈上台阶、转身坐下来时,头脑中只剩下怒火催生出的报复欲。我可以说是满怀恶意地问它:“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篇漫画故事,对吗?”
不管这把椅子为何而来,不管是谁引导了这一切,我想告诉它盒子里的猫没那么无知,也从未对自己做过的选择感到后悔——我是有罪,就让我下到地狱里去的同胞站到我面前来一一罗列吧。
莫比乌斯椅没有立刻给我答案。
它漆黑的表面篆刻有银白色的纹路,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柔和稳定的光。我猜想莫比乌斯椅的上一任主人密特隆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被人从椅子上拖了下来。僵持几秒钟后,我脑海中显现出莫比乌斯椅的回答:
“错。”
下一刻,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哥谭。
凝固的万事万物重新开始流动,爆炸却消失了,时间从旭日东升变为沉沉黑夜。我半跪在哥谭一座普通居民房的尖顶上,身着制服,脚边摆着六个系有精致粉色蝴蝶结的绿色礼盒。
耳边响起阿尔弗雷德的声音,他是在对我说话,或者说对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的小托马斯·韦恩说话:
“理查德少爷死的时候您在哪?”
我身体还保持着向前冲刺的起始姿势,头脑一片空白,暂时没能理解阿尔弗雷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我身后响起另一道陌生男性声音:
“你好。”
我霍然回头,手中从不离身的武器蓄势待发,但当我看到和我打招呼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时,又不由得将手臂放下了。
我尽量客观地描述这一场景:哥谭市上空飘着一个蓝色的裸|男。
第70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