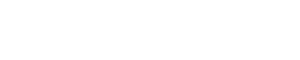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72节(1/2)
作品:《[综]累金铄骨+番外》
。
他消失后,我买下了那所房子,把他养在楼上阳台的常春藤拿下来照顾。
我出差回来,发现床边的刀痕和缺失了的手稿。
常春藤死掉了。
说永远不会回来的富酬回来过。
我想刀刺中了我的动脉,我的血液在飞速流失。
世界从我身旁波涛般地汹涌掀起,又狂风般地极速逝去。
我听到隔壁的动静。
白天已经表现得那么殷勤又错漏百出了,只好强忍着不去看他。
我以为我忍得住。我放下手里的营生去了隔壁,敲门入内,见到他之前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他会有这种精神状态。
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狡猾、清醒而目标明确的,压抑着悲伤,不显露内心,你看他脆弱易折,同时知道他不会轻易破碎。
而我眼前的是一个被压垮却重建不能的人。
他从污浊的水中站起来,忽然反应很大,说别提她。
她……是美惠吧。
他不计力度的撞破自己的额头,那种劲儿是真正失去理智的疯子特有的,他是有用生命冒险、孤注一掷的疯劲儿的,只是之前用市侩钻营的表皮矫饰得完美无缺。
医生医不好他,照粗略诊断看,他有不少年岁可活,却不肯照顾好自己。过得舒坦向来非他所愿,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我见他十分不舒服,在发抖,一时冲动,没多想就脱下外套给他披上。
眼下是我与他重逢以来最近的距离,我这才发现,他似乎病得厉害,眼睛也坏了。
震惊之下,问话脱口而出,还以为一开口准会暴露,在心里为解释自己怎么在这组织措辞。
但是他不记得我。
路程很赶,为了不等隔天下一班周日的船,我们两人晚上挤睡在一张一米半宽的床上。
好几个晚上我睡不着,望着他单薄的背,很想伸出手去,他因药物睡得极沉,若触碰他,他也不会有知觉,但我只是和他背对背的侧卧着,从未逾距。
我感到呼吸困难、缺氧、正濒死。
躯壳死去的过程中,我的灵魂空前活跃,感受到了活着时不会有的生的挣扎和喜悦。
绝大多数历历在目的回忆都是关于他的。
美惠的遗书之所以留下富酬的名字,我猜是不忍心让其被火烧掉。
我睡不着,他依旧沉睡着。我似梦似醒的倚坐在床头,估计这艘船何时靠岸。
他现在多病无依,我大可阻止他眼睛康复,带他辗转于一艘又一艘轮船,把他永远困在海上。
只要我做就能得到,但是,我究竟想得到什么呢?
忽然床随船晃动倾斜了下,距离缩得更短了,他翻过身面朝我,无意地几乎闯进了我怀里,眉头微皱,眼睫湿漉漉的,做着必然会遗忘的梦。
彼时彼刻所有念头都灰飞烟灭,我不祈求他的梦中有我,而那之后,每时每刻,我都处在怀中有他的时间。
我的原罪像一条长蛇绞紧了我。
表面上我有选择的权利,身后全是退路,实则自我背井离乡追寻而来,就注定了什么都得不到,已有的也失去。
我于痛苦与 Y_u 望之间徘徊,被自己偶尔闪现的 Yi-n 暗念头吓到。
后来我想明白,这里面没有爱的问题,因为爱充满我的时候,我是宁静的。
要以何种方式爱,我其实已有答案。
他给过我不止一天,不止一个吻,不止一个拥抱,很多东西存在过就够了,不应希冀更多。
只是这样,终究心有不甘。
星期五,富酬预计星期五将恢复视力。
届时他睁开眼看到我,我可以坦白告诉他我的付出和牺牲,他可能会责怪我说谎,会愧疚,会感动,会同我在一起,唯独不会爱我。
我离开了。
我离开的原因就是我来的原因。
父母、雅臣还有弟弟们,我为了一场从未见过的烟花离开并舍弃了他们。
真奇怪,我想我是为了这场苍白而虚无的烟花存在的,并且一点都不觉得不值。
今天有一次十分常规的烟火大会,大家去看烟花,只有我置气不去,我忘了因为什么生气,兀自委屈着,等人们回来,谈论盛大的漂亮的烟花,我难受又遗憾。
往后无论我看过多少烟花,心目中最美的烟花永远是没看到的这场。
第72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