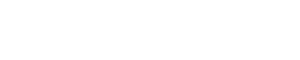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19节(1/2)
作品:《[APH黑塔利亚同人]The Legend of 1917海上钢琴师》
会把美酒交给你来当水喝!’
我们聊了很久,幻想了他未来那个不走运的另一半的模样,我指天发誓他的老婆一定想搬到你家里去。
他说他会穿着你送给他的驼毛大衣,哪一年的新年礼物?因为在船上根本没有必要穿。
我嘲笑他,现在他肚子上的赘肉会让衣服根本扣不上扣子。
不过一切还好,他穿上大衣,围着长长的围巾,戴着帽子,像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旅客。精神,帅气,酷。我们都站在甲板上,每个人和他拥抱。谁都知道,下次我们再见到他,就是在报纸上啦。
‘再见,1917!’
‘替我向百老汇问好!’
我们趴在船舷上,看着他回头向我们挥手,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准备离开家,就是这种感觉吧。他开心的挥手告别,走向下船的扶梯。
梯子一共46阶,一个小伙子告诉我,总有人会注意到那些不相干的事情。
他,1917,走到一半,站在船与陆地交界的中点,脚下是大海。他停住了。
时间定格了一样。
码头上人来车往,甲板上交头接耳,只有他,一动不动。
‘哦,他又怎么了?踩到狗屎了?’我实在不耐烦。
‘说不定忘拿什么东西了?’
‘他难道是去撒哈拉沙漠探险吗?什么东西纽约买不到?’
‘也有可能突然脑子轰的一下,忘记带上下船的理由?’
我们安静到听着海鸥鸣叫着划过被高楼刺破的天空,那个高大的傻子就站在那里,距离土地只有不到30步,每一只脚只用碰到扶梯十几下!
我都看烦了。
他终于有了动作,而不是被谁速冻起来。
他摘下帽子,甩向空中。圆帽旋转着,像是要飞向陆地,可又转回来,最后落到海面上。他转过身,我看到他摇摇头,带着他一直有的孩子一样的微笑,走上扶梯。
对的,Yau,他又回来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又落幕了。
你寄的明信片都交给他了,很漂亮的风景,我们都赞同你的品味。
你的朋友”
伴着钢琴曲,东方人打开最后一封信。
“Yau: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脚下的地面不再晃动。对,我已经回到家里,离开了那条船,和航海的岁月。
1917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要下船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他怪怪的, Xi_ng 格孤僻,沉默不语,不知沉浸在什么事情里面不能自拔——后来想想,他平时也经常如此,可能是我们自己太过敏感。我们把他想下船的事情看得太重,这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次平常的‘一时 Xi_ng 起’。
头等舱的客人越来越少,船长开放了二等舱的旅客,允许他们也来到舞厅。我们穿着整齐的礼服,在那群人里面吹奏乐器,看起来真可笑。我们像是街头卖艺的。
和任何昙花一现的明星一样,渐渐的,也没有什么人提起1917和他战胜爵士乐创始人的传奇经历。
我不能说是1917退步了,他在不断探索,在发展着自己,可是我们疲惫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调调,哪怕有再多的变奏,我们总是会注意到那些不变的东西,然后打个哈欠。大概我们也已经欣赏的足够了。
没有别的刺激。
我们的听众也变得不容易被打动了,他们在闲聊,在放松自己,或者在筹划下一步的拼搏,最后用半只耳朵听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会有一两个懂行的问:‘哦,这个弹琴的,他发表过什么唱片?销量如何?’
不,一张,可能一张都没有。
‘哦,我以为是个大家呢,太可惜了!’他们会这样说,‘知道吗?H. F. 琼斯的最新CD正在大卖。哦,那简直是仙乐,神曲!果然是无人能敌的天才!’
事情就是这样,我已经没有精力去骂那个傻瓜了。
我很高兴他变得固执而孤僻,否则他会整天提着酒瓶子去殴打那些听众,这样太糟糕了。我宁愿他像头听不懂人话的熊,抱着一棵玉米就开心无比。
最后,前半个月,我拿走了我的薪水,离开了康缪尼司特号。
我回到我的太太身边,可能今年内,我们会要个孩子。
我也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在哪个音乐学校谋个职位,或者去参加哪个乐队,私下再教两三个学生。
第19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