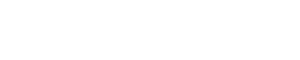第23节(1/2)
作品:《对牛谈情》
是百般湮灭不了。
与许戡一样,他临走时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能否按时回来,还不明确。要是拖延的时间久了,被退学都有可能。况且落下的功课,没有人愿意无偿给予补给。在两个饭店里的打工,也因此而被取消。估计返回现代后,他就会被无形地给炒了。那样的话,日后最基本的生计开销又将如何解决呢?
而比起这些,母亲的情况最让他揪心。瘫痪在床的她,一切生活都不能自理,而自己又住宿在大学里,平时都得靠他人照料。被林菱霏要挟搬离原住址后,为了不将消息透露出去,便将原来的护工给换了。这回临走前,预先付给新的保姆三个月的薪水,不知她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好好对待母亲?
苦恼就会钻渺小快乐的空隙,侵入他百密一疏的心绪。放眼周围,没有什么同类人。为数不少的大学生们无非在赖床,逃课,作弊,上网,恋爱中虚度光 Yi-n 。即使在全国重点大学。尤其是城市中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相对于自己来说,舒适而无忧无虑。
是什么造成了他的艰难和辛劳?兴许是父亲的离开,母亲的重病所致。从小到大,看到同学们都有父母来接送,动辄提及父母,舒流萤的心里总是酸涩地不是滋味。当高中同学问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他的嘴像被缝上了似的,怎样也说不出实话,亦没有说谎的心机。
思绪远远地飘渺,调动起尘封的记忆和沉睡中的脑细胞。
——
是的,我的父亲,据母亲模糊的言语,是做不光明生意的。也许仅仅是走私香烟碟,也许仅仅是贩卖毒品军火。不清楚父亲的工作 Xi_ng 质,因而我也不明白,为何从小我和母亲便是见不得人的那种人。仅仅是活着的人而已。
我们住在朝北的, Yi-n 仄 Ch_ao 湿的小阁楼内,倒也不是见不着阳光,而是一到冬天,整间阁楼冷得像冰窖一般。母亲下班回家,便坐在阁楼的天窗下,埋头织羊毛手套和外套——送给别人以得到些许好处;织给我,防止我的手生冻疮。母亲说,练竖琴的人,一双手格外重要,万一有什么瑕疵,以后弹起琴来,多少有些上不了台面。她偶尔和我提起这些琐事,隐忍着头颈和肩膀的酸痛,不停地织啊织……
她的手已不复昔日的光彩,关节上都是红红的印记。指尖因拨弦而磨出的软茧,都被家务的辛劳所覆盖。而我的手,完好无损。茧子是那样的柔软,好像是新生的肌肤。
母亲年轻时,是著名乐团里的竖琴演奏员。家境亦是书香门第。样貌放到今日来看,依旧是毫不张扬的,静静的美丽。至于父亲的模样,我只在一张黑白相片里见过。俊美挺拔中带着些狠戾的气质。我看了又看,总觉得自己不像父亲,似乎也不像母亲。
家里的一架旧竖琴,便是她拼命从家里带出来的。自从她不幸的生活开始,她就再也不碰那件乐器,仿佛它臭不可闻。她自己弹不成竖琴,却寄希望于我身上,极其认真,甚至是严苛的调教。果真遗传了母亲,我在骨子里,热爱这件乐器。当指尖轻拨琴弦时,乐音仿佛带走了所有的苦难。我猜,父亲一定是在某场音乐会上,认识了我的母亲。
不知是何种孽缘,造就了她与父亲的相识。家里自是一万个不同意。最后母亲与家里彻底断绝了关系。也不知是母亲跟着父亲私奔了,还是父亲强行带她逃走。我想,其中总是因为“伟大”的爱情的作祟吧。
然而父母之间的爱情,保鲜期是那么的短,腐烂起来的速度亦叫人扼腕。这叫我不由相信许多人所说的,爱情是最苍白无力的精神自 We_i 。
在母亲生下我后,父亲把我们迁移到闸北的一个偏僻弄堂里。大概是怕种种麻烦找到无有能力的妇孺。日久,他渐渐地不再来看望我们,只是几个月寄一次生活费过来。我的童年便是在 Yi-n 寒和滞涩中度过的。而母亲的青春,亦是在孤寂与绝望中逝去的。她从来没想到再找个伴侣,她说过,只一心把我培养成人。
不记得是何时,我找东西时,在隐秘的抽屉里翻到一把手枪。问了母亲,才知是父亲送给她的。明知她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难不成叫她危难时拿起手枪自卫?我觉得很好笑。却也不敢轻易擅动。在小学里学过两年的长枪 Sh_e 击训练,了解手枪的操纵难度。这把59式的陈旧手枪,不知历经了多少光 Yi-n ,而后来使用起来仍是简便。或许得归功于我幼时的专业训练吧。有了它,在第一次和敌人对峙的过程中,侥幸而退。可惜,最终还是叫他人给毁了。当然这是后话。
第23节(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